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在公布春季预算时声称,他的计划都是关于增长的。对反对党领袖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来说,增长是他的关键“使命”。
更高的增长——正确的增长——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但是英国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好。自千禧年以来,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急剧放缓。如今,这一比例低于其他富裕国家。
然而,这只是该国面临的多方面问题之一。贫困水平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倍。英国的贫富收入差距比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要大。关键的公共服务资源一直匮乏。
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对这些多方面的危机以及如何解决危机无话可说。其传递的信息似乎是,如果没有更快的增长,就几乎无能为力——最近的历史表明,这种立场远远不能解决日益加剧的贫困或社会脆弱性问题。
我的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经济活动的收益越来越多地被少数富有的精英阶层所攫取,而许多战后的社会收益却被逆转了。自2010年以来的滚动紧缩措施大大加剧了这种情况。
英国亲富反贫的偏见是其支离破碎的经济和社会的核心原因。近几十年来,决定国家实力的关键因素——创新率、投资、劳动力技能和社会支持质量——都落后于我们的竞争对手。
造成这种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的话)是,商业活动在错误的国家政策的帮助下,越来越倾向于快速致富。这种少数精英“企业榨取”的过程,是以长期财富创造为代价的,而长期财富创造本可以增强经济韧性,服务于共同利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声称,弱化国家监管会使市场更具竞争力。然而,更宽松的规定赋予董事会更大的自由,使他们能够巩固企业权力。从银行、审计到制药和住宅建筑,关键市场现在都由少数少数拥有和控制的公司主导。
许多大公司已经变成了所有者和高管的摇钱树。董事会采取了各种反竞争手段,从消灭竞争对手到串通价格。这是一个多世纪前美国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所说的“市场破坏”的回归。
这样的做法排挤了那些具有更大社会价值的创新。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他们一直是英国低工资、低生产率和高贫困率经济的核心驱动力。近几十年来,他们的回归已成为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主要障碍。
私人投资和工资没有得到提振,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利润(在疫情期间继续增长)被抽走,以不成比例的方式支付给了股东和高管。
英国工会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 2019年的一份报告称,在从2015年开始的四年内,富时100指数成分股公司四分之三的利润以回购和股息的形式返还给了股东。
英国的贫困水平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倍——斯图尔特·兰斯利(Stewart Lansley)
随着海外机构投资者(尤其是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越来越多地持有英国企业,这些资金流入英国养老金和保险基金的比例微乎其微,也没有回流到英国国内经济。
1896年,颇具影响力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区分了为全社会带来收益的“增值活动”和造福于强大少数群体的“榨取性”或“挪用性”商业行为。
挪用在19世纪是司空见惯的事。随着权力集中的回归,这种做法再次成为主流。这些行为包括操纵金融和产品市场,以及从金融交易中榨取收益。
私募股权投资者财团寻求快速和膨胀的回报,已经收购了许多上市公司(从汽车集团AA,零售商Topshop, Debenhams和Morrisons等等)。在许多情况下,包括Debenhams和Topshop的所有者阿卡迪亚集团(Arcadia Group),这削弱了长期生存能力。
重要的公共服务现在正在接受类似的待遇。曾经主要由公共机构提供的社会保障,已成为私人收购行业的主要目标。其结果是,相当大比例的公共资金实际上被这些新提供商抽走了。
这些趋势对社会运作方式的影响大多是破坏性的。例如,财富积累过程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资源从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需求转向满足最富有的人的生活方式。
其结果是,我们正在看到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所说的“私人富裕和公共肮脏”的重现。自2010年以来,英国至少有1000家Sure Start儿童保育和家庭服务中心倒闭。议会开支的削减导致4500多名青年工人失业。
将英国低水平的社会投资与激增的私人飞机需求相比较。可用于建造社会保障房的土地已被豪华开发项目所吞噬。
1945年,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出任英国首相时,他领导的工党政府接手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毁的社会。公众渴望变革。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在1942年警告称,英国需要的“不仅仅是修补”,但他忽视了英国历史性的债务危机(为战争买单的结果)。
相反,他推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社会支出计划,优先于促进私人消费。具有开创性和受欢迎的改革包括国民医疗服务,一个全面的、强制性的和普遍的国民保险制度,以及家庭津贴福利。
如今,两大主要政党的战略都包含着一个核心矛盾。仅靠更高的增长,即使能够实现,也不会带来一个更强大、更公平、更平等的社会。这需要一项变革性的计划,以解决如此多的现代商业战略导致不平等的方式。在1945年,这不仅仅意味着“修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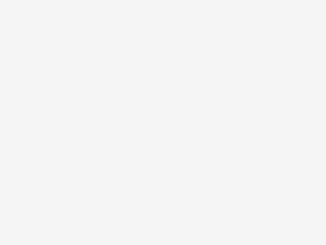
 皖公网安备 34011102002444号
皖公网安备 340111020024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