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9年里,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对印度日益增长的增长潜力押下重注,而不是其他国家。证据描绘了印度经济发展的另一幅图景。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和(私人)投资情况的关键指标,在印度一直处于波动趋势。GFCF的高波动性也反映了企业投资需求疲软和产能利用率降低。虽然服务业在大流行后的复苏情况下表现相当不错,但工业生产和制造业增长的表现仍然严重不足。
贷款增长或可贷款资金供应的增加可能有助于GFCF数字的波动上升,但“实现的增长潜力”仍不清楚,因为这些数字并未积极促进可持续的更高增长轨迹。可贷资金的增加,将是印度央行主导的货币政策性质和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结果。在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中,较高的利率(影响借贷模式)将对银行向私营部门提供廉价信贷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假设对这种信贷有需求)。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这些数据,就会发现,从2019年底到2022年年中,印度的核心通胀率一直高于银行贷款增长率,从那以后,贷款增长率一直高于通胀率。过去几周的情况表明,在印度央行(利率)的现状下,较高的通胀率如何威胁到银行继续提供更多信贷的能力。在食品通胀方面,价格模式仍然极不稳定(反映在与均值的较大差异上),这使得平均收入公民的基本家庭消费篮子更加昂贵。
这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在打破核心通胀趋势的过程中,自2014年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在中低收入/消费阶层收入停滞和下降的情况下,CPI持续上涨。在农村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物价上涨使低收入者的处境更加糟糕。这也严重损害了印度城市中等收入者的储蓄能力,而储蓄对于在银行创造流动存款至关重要(银行最终利用存款资本来设计信贷工具和信贷创造能力)。
另一方面批发价格指数(WPI)从2022年后开始急剧下降,这表明影响制造业/工业部门的需求侧问题加剧了通货紧缩螺旋。私营企业发现“乐观”的理由越来越少(与总理和财政部长对印度的乐观言论相反),而且在消费者和资本品的可预见需求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回升的情况下,它们也没有向新的产能投入大量资金。
除此之外,大多数私人投资都是由具有垄断优势(来自现有财富禀赋)的精选大资本商业集团(阿达尼、安巴尼)锚定的,目的是收购“新的资产领域”用于业务扩张,而不是为了投资于新的能力建设以促进增长扩张。它反映了大资本和印度政府之间联盟的倒退状态(标志着高层裙带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贸易方面,出口有所增长,但以进口为代价。经常账户占GDP的比例恶化至2014年之前的水平。这反映出印度的工业和贸易政策未能将重心转向具有竞争力或比较优势的领域。印度快速增长的服务业不仅有潜力为出口做出更大贡献,也有潜力为就业和整体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2024年大选后的挑战
如果必须确定下一届政府(无论谁组成)在优先考虑经济治理和社会凝聚力(作为健康经济的先决条件)方面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那么将涉及以下三个:
第一提高所有人的宏观就业率,第二以可持续的方式增加各部门的私人投资(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创造就业的领域),第三应对核心通胀和食品通胀的巨大差异,同时管理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以制定可能奏效的财政整顿计划。
在莫迪执政期间,印度与失业增长时代的幽会只是被延长了。高薪工作(在有组织的部门)的增长并没有以预期的速度或速度发生,也没有成为政府在财政和预算分配中优先处理的一部分。
相反不断增加的政府资本支出是以降低MGNREGS等以就业保障为基础的福利计划的拨款为代价的。各国的资源和工具有限,无法将资源用于工人密集型增长计划或通过自己的财政干预创造就业机会。
在莫迪-西塔拉曼的领导下,中央政府甚至没有承认“创造就业”(和高失业率)是一个挑战,因此必须做出很多改变。以就业为重点的社会保障计划也是当前最迫切的需求之一。
至于私人投资,私营部门未能与政府财政政策的“乐观”推动保持一致。简而言之更高的资本支出并没有真正吸引私人投资。在PLI计划上花费的数千亿卢比也没有带来正增长,也没有带来就业红利。
对政府债务的担忧需要更密切的关注。随着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激增,政府继续挤压各州的财政自主权和借贷能力,整体外债借款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令人担忧。这不仅让人质疑预先设计的财政整顿计划的“有效性”,也让人质疑政府支出偏好的可行性。
无论是印度国防工业联盟还是印度人民党/全国民主联盟,对经济状况进行诚实、批判性的反思,以及为2024年后制定可行的中长期行动计划,解决所讨论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对于实现对印度增长/发展潜力的乐观态度仍然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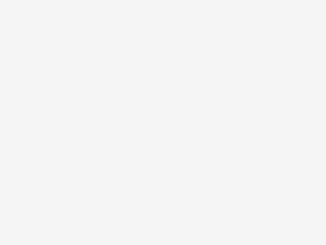
 皖公网安备 34011102002444号
皖公网安备 34011102002444号